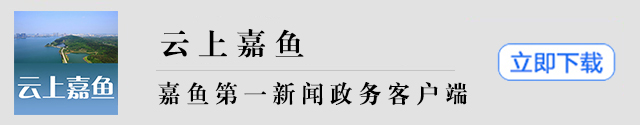人都是饮故乡水长大的,因而对于她总是怀着一份深深的眷恋之情。“美不美,乡中水”,我当然也是这样。
我的祖籍虽是湘中名区衡山,却生长在长江边的嘉鱼县,故本文所说故乡,指的是嘉鱼某片低洼的湖沼之区——一个被乡亲们称为“水眼子”的小村子。村子四周被三四米高的土堤围护着,围堤内有三千亩左右水田和一千多村民。村南村北有两条几十米宽的长沟,方圆几十里的雨水,从这两条大沟汇入金水河,然后流进长江。记得小时候,围堤内还有一大片未开垦的野湖,湖中泥深不知底,有时牛陷进去,往往需借助人力,才能从污泥中爬出来。冬天,田中一片白水,寒光闪闪,冷气逼人,散布在田中的稀稀落落的人家,如一处处湖中孤岛。即使暖日当空,整天也是寒瑟瑟的。从一家到另一家,不是过独木桥,就是走田埂,一不小心就掉进水田。
据记载,这里曾是长江故道。陆放翁《人蜀记》描写这一带“无复居人,两岸皆葭苇弥望,谓之百里荒”。可知直至南宋时代,这儿仍是一片黄茅白苇,鸥栖凫戏的荒凉之地。而我们村这块仅仅几平方公里的地方出现人烟,更是晚近的事。1935年,金水闸修成,湖水不再与长江共消长,当局招募民工开荒,于是不少湖南青年一根扁担挑两只箩筐千里迢迢徒步来到这里垦荒谋生。而在离故乡不到一公里远的地方,很早以前就有了居民,因为他们居处较高,我们称他们为“墩子上人”,而他们则称乡亲们为“湖南人”,称这地方为“湖里”,称这里的民居为“湖南棚子”。多少代中,这里都是“墩子上人”捕鱼挖藕的地方。
故乡水多,水产品自然十分丰富。那时节,生产队把稍宽的水面分到户,为了增加点收入,家家户户都在沟中放养菱角。秋风送凉时节,菱角熟了,人们往往卷起裤筒,站在沟边水中,一手攀树,一手摘菱角吃,吃完再把菱角苗平放如初,待到采菱女坐着莲筏子或者脚盆采菱时,才发觉绕茎尽是空蒂,于是无可奈何地骂那“吃了烂嘴巴”的人。和菱角比起来,荷藕可少得多,因而吃莲蓬相对难些,虽说野莲无主,但近岸的莲蓬被路人随手摘尽,剩下的都藏身在水中央那亭亭玉立的荷叶和粉态盈盈的荷花间,鼓起眼睛望着行人,行人却只有垂涎的份儿。还是放牛娃有办法,他们往往乘放牛的机会,脱衣下水,轻易地把那美味变为腹中之物。虽然身上被荷叶划出一道道血痕,也毫不后悔。团团的平躺水面的鸡蛋菱,每条稍大的水沟中总有一两处,鸡蛋菱的圆叶,大如面盆,呈紫红色,叶下结圆形果实,形如鸡蛋,故名。可食,但吃起来颇麻烦,因为叶、茎、实均多刺,因而它们往往被猪享用。
俗话说,“有水就有鱼”,故乡水产占鳌头的,无疑要数鱼。湖中、沟塘多鱼是必然的,就是正被耕整的泥田中,也常有鱼可捉。夜雨初停春云沉沉的早晨,在还未开犁的白水田中,远远看到有银白色的东西在动,近前一看,原来是一条大鱼从沟中戏水上田,被搁浅在烂泥上,正等待人们下田去拣哩!有时田也不用下,因为落春雨时,鱼往往跃出沉渊在田埂缺口流水处斗水。有时被卡在缺口里,既不能进,又不能退,只有乖乖当俘虏的份儿。不过这要运气特别好。有一位擅长撒网捕鱼的老农说,有一次一网撒下去,网脚子沉不下水。因为被朝天乱拱的鱼头顶住了。这话虽夸张至极,但也多少反映出我们那儿多鱼的事实。1964和1969年村里被水淹时,救济粮不够吃,人们就吃鱼煮萝卜,或者把小鱼煮成稀粥充饥,直吃得人们满身满屋鱼腥味,闻鱼味便远而避之。很长一段时间,鱼都是不受欢迎的食物。至于时下卖大价钱的甲鱼、乌龟、黄鳝之类,有的人家至今仍不许它们上饭桌。
不过话说回来,水有利人的一面,也有害人的一面,比较起来,甚至害大于利也说不定。在山寒水瘦的严冬,沟中水仍是满满的。因为水位高,好点儿的树种没法成活,故家乡多的是柳树、意杨之类,单调极了。每一个成年人小时候几乎都有掉进水中被人救起的往事,小孩、甚至不会游泳的大人失足落水被淹死的惨剧时有所闻。这里从不怕天旱,天越旱,收成越好,而雨却很少有受欢迎的时候,特别是黄梅时节那“聋子雨”(指没有雷声的闷雨),直落得人们心中惶惶,魂不守舍。我小时候亲历的两次水灾就是这时节发生的。我的心中至今仍留着这样的图景:绿油油的菜园和大片大片鹅黄色的稻田全被埋在水底,房屋倒塌水中,或者剩下几根木柱顶着稻草盖,艰难地经受着风浪的冲击。人们有的搭个草棚子住在堤上,任日晒水蒸,有的迁居他乡,寄人篱下。个别人家还得行乞度日。至今,水仍是村里人的心头大患,“今年会淹吗?”仍是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因为历史上多次水灾,乡亲们远远说不上富裕,因为怕遭水灾,人们不敢全身心地建设家园,甚至不愿多置家具,怕多余的东西成为逃灾时的拖累。村里姑娘相婆家,首要一条是离开这“水眼子”,“讨”来的媳妇经过几次折腾后,往往后悔得直跺脚:早晓得这样,决不嫁来!话又说回来,虽然渍水几乎每年都有,人们每年得吓一跳甚至于吓几跳,但垮围堤的事却三十多年没有发生过,尽管堤外肆虐的渍水常常高过屋檐,其吞噬小村子的企图却一次也没有得逞。
水的恩惠,曾给生活于艰难年代的人们许多帮助,随着艰难年代的远去,水中的丰富蕴藏也早成历史。现今淤塞得厉害的沟中,光光的,一无所有,甚至连丝草也难见一根了。什么时候,水之害远去而水之利重新回到人们生活中来呢?
都是饮故乡水长大的,因而对于她总是怀着一份深深的眷恋之情。“美不美,乡中水”,我当然也是这样。
我的祖籍虽是湘中名区衡山,生长却在长江边的嘉鱼县,故本文所说故乡,指的是嘉鱼某片低洼的湖沼之区——一个被乡亲们称为“水眼子”的小村子。村子四周被三四米高的土堤围护着,围堤内有三千亩左右水田和一千多村民。村南村北有两条几十米宽的长沟,方圆几十里的雨水,从这两条大沟汇人金水河,然后流进长江。记得小时候,围堤内还有一大片未开垦的野湖,湖中泥深不知底,有时牛陷进去,往往需借助人力,才能从污泥中爬出来。冬天,田中一片白水,寒光闪闪,冷气逼人,散布在田中的稀稀落落的人家,如一处处湖中孤岛,即使暖日当空,整天也是寒瑟瑟的。从一家到另一家,不是过独木桥,就是走田埂,一不小心就掉进水田。
据记载,这里曾是长江故道。陆放翁《人蜀记》描写这一带“无复居人,两岸皆葭苇弥望,谓之百里荒”。可知直至南宋时代,这儿仍是一片黄茅白苇,鸥棲凫戏的荒凉之地。而我们村这块仅仅几平方公里的地方出现人烟,更是晚近的事。1935年,金水闸修成,湖水不再与长江共消长,当局招募民工开荒,于是不少湖南青年一根扁担挑两只箩筐千里迢迢徒步来到这里垦荒谋生。而在离故乡不到一公里远的地方,很早以前就有了居民,因为他们居处较高,我们称他们为“墩子上人”,而他们则称乡亲们为“湖南人”,称这地方为“湖里”,称这里的民居为“湖南棚子”。多少代中,这里都是“墩子上人”捕鱼挖藕的地方。
故乡水多,水产品自然十分丰富。那时节,生产队把稍宽的水面分到户,为了增加点收入,家家户户都在沟中放养菱角。秋风送凉时节,菱角熟了,人们往往卷起裤筒,站在沟边水中,一手攀树,一手摘菱角吃,吃完再把菱角苗平放如初,待到采菱女坐着莲筏子或者脚盆采菱时,才发觉绕茎尽是空蒂,于是无可奈何地骂那“吃了烂嘴巴”的人。和菱角比起来,荷藕可少得多,因而吃莲蓬相对难些,虽说野莲无主,但近岸的莲蓬被路人随手摘尽,剩下的都藏身在水中央那亭亭玉立的荷叶和粉态盈盈的荷花间,鼓起眼睛望着行人,行人却只有垂涎的份儿。还是放牛娃有办法,他们往往乘放牛的机会,脱衣下水,轻易地把那美味变为腹中之物。虽然身上被荷叶划出一道道血痕,也毫不后悔。团团的平躺水面的鸡蛋菱,每条稍大的水沟中总有一两处,鸡蛋菱的圆叶,大如面盆,呈紫红色,叶下结圆形果实,形如鸡蛋,故名。可食,但吃起来颇麻烦,因为叶、茎、实均多刺,因而它们往往被猪享用。
俗话说,“有水就有鱼”,故乡水产占鳌头的,无疑要数鱼。湖中、沟塘多鱼是必然的,就是正被耕整的泥田中,也常有鱼可捉。夜雨初停春云沉沉的早晨,在还未开犁的白水田中,远远看到有银白色的东西在动,近前一看,原来是一条大鱼从沟中戏水上田,被搁浅在烂泥上,正等待人们下田去拣哩!有时田也不用下,因为落春雨时,鱼往往跃出沉渊在田埂缺口流水处斗水。有时被卡在缺口里,既不能进,又不能退,只有乖乖当俘虏的份儿。不过这要运气特别好。有一位擅长撒网捕鱼的老农说,有一次一网撒下去,网脚子沉不下水。因为被朝天乱拱的鱼头顶住了。这话虽夸张至极,但也多少反映出我们那儿多鱼的事实。1964和1969年村里被水淹时,救济粮不够吃,人们就吃鱼煮萝卜,或者把小鱼煮成稀粥充饥,直吃得人们满身满屋鱼腥味,闻鱼味便远而避之。很长一段时间,鱼都是不受欢迎的食物。至于时下卖大价钱的甲鱼、乌龟、黄鳝之类,有的人家至今仍不许它们上饭桌。
不过话说回来,水有利人的一面,也有害人的一面,比较起来,甚至害大于利也说不定。在山寒水瘦的严冬,沟中水仍是满满的。因为水位高,好点儿的树种没法成活,故家乡多的是柳树、意杨之类,单调极了。每一个成年人小时候几乎都有掉进水中被人救起的往事,小孩、甚至不会游泳的大人失足落水被淹死的惨剧时有所闻。这里从不怕天旱,天越旱,收成越好,而雨却很少有受欢迎的时候,特别是黄梅时节那“聋子雨”(指没有雷声的闷雨),直落得人们心中惶惶,魂不守舍。我小时候亲历的两次水灾就是这时节发生的。我的心中至今仍留着这样的图景:绿油油的菜园和大片大片鹅黄色的稻田全被埋在水底,房屋倒塌水中,或者剩下几根木柱顶着稻草盖,艰难地经受着风浪的冲击。人们有的搭个草棚子住在堤上,任曰晒水蒸,有的迁居他乡,寄人篱下。个别人家还得行乞度日。至今,水仍是村里人的心头大患,“今年会淹吗?”仍是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因为历史上多次水灾,乡亲们远远说不上富裕,因为怕遭水灾,人们不敢全身心地建设家园,甚至不愿多置家具,怕多余的东西成为逃灾时的拖累。村里姑娘相婆家首要一条是离开这“水眼子”,“讨”来的媳妇经过几次折腾后,往往后悔得直跺脚:早晓得这样,决不嫁来!话又说回来,虽然渍水几乎每年都有,人们每年得吓一跳甚而至于吓几跳,但垮围堤的事却三十多年没有发生过,尽管堤外肆虐的渍水常常高过屋檐,其吞噬小村子的企图却一次也没有得逞。
水的恩惠,曾给生活于艰难年代的人们许多帮助,随着艰难年代的远去,水中的丰富蕴藏也早成历史。现今淤塞得厉害的沟中,光光的,一无所有,甚至连丝草也难见一根了。什么时候,水之害远去而水之利重新回到人们生活中来呢?(王桂华)
此文选自由嘉鱼县文化和旅游局、嘉鱼县作家协会联合编著的《南有嘉鱼》丛书。该书已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发行。
来源:南有嘉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