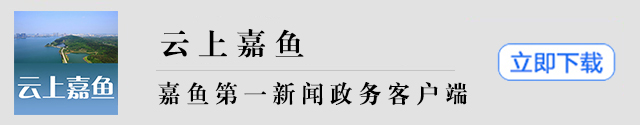每当一年一度江汛到来之际,在武汉长江上游75公里处,有一个无言的卫士在默默保卫着大武汉的安全。这个卫士是谁?就是嘉鱼县的簰洲镇和它那有名的“簰洲曲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簰洲湾”。
为了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些,让我们打开三百五十万分之一的湖北分省图,只要您把视线从武汉市沿长江向西南移动大约一指宽的位置,就能看见长江在这里绕了个大弯。在弯子里,有一座很繁荣的集镇叫簰洲镇,也就是郭沫若先生在他的《洪波曲》中提到过的“簰洲——在地图上长江大转弯的那个地方。”也许您要问:这长江大转弯跟武汉卫士有什么关系呢?“武汉卫士”又是怎么回事呢?好,现在就让我从头道来。
在古代,簰洲地区本不像现在这个葫芦形状的。据《禹贡》版图载,它是作为一座无名沙洲“存在于长江之中”的。到了汉代,它才有了正式命名:沙阳洲。 当时,这沙阳洲把长江分为南、北两条江流。到了晋初,南江北移,由于古老南岭残丘的抵制作用,迫使江水转向西流30华里,旋与东荆河汇合而转向北流,后又由北而转向东南,绕过整个沙阳洲回到与原南江航道相平行的位置。后经历代河道变迁,特别是宋代修筑堤防以后,江流日趋稳定。到了民国初年,合镇垸大堤竣工,簰洲与老官地带相连,原先航道残留的決套完全淤成陆地,便形成了现今江流的葫芦形的半岛地势,而长江呢,就形成了这一段环形套似的“簰洲曲流”。
是的,在这一千多年的河道变迁中,南岭残丘是胜利者。为了不让喧嚣的江水破坏它宁静的环境,它成功地将长江扭曲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性情耿直而暴躁的大江,岂肯绕着弯儿多走110华里的冤枉路?于是它满怀怨愤地日夜冲击那弯弓似的江岸,而簰洲镇恰好首当其冲。
至于簰洲镇是怎样在这个葫芦形半岛上发展起来的,说来话就长了,这里只能作一个简略的说明。据载,簰洲地区属古沙阳洲,是古云梦泽冲积平原的一部分。此地气候四季分明,土地十分肥沃,先秦时就有人来此开垦,汉初便开始形成商埠,明初已成为邻近各县及川湘两省的贸易市场及各类物资的集散中心。簰洲本来地处长江南岸,因有30里西流水而成了北岸。岸陡水深,北风难袭,是难得的避风良港,往来船只都喜欢在此停靠,特别是从四川、湖南下来的竹排、木筏停靠最多。因此,到了元代人们便称之为“簰洲”。后经明清两代的经营、发展,到了清末民初,簰洲已成为一座相当繁荣的商埠了。它不仅拥有48条街道,4万多居民,仅槽房、榨房就有100多家,各种商行、商店近千家。沿江看去,但见高墙林立,长簿蜿蜒,汽笛啸江,人声催浪,真可谓工商繁盛,各业俱全,车载船运,水陆两旺,难怪一时享有“小汉口”之美誉!
谁能想到、谁能想到啊!远从明代正德以来,一种不祥的阴云开始笼罩簰洲。因其地属长江冲积平原,地层大量含沙,江涛冲刷,坡岸洗空,开始发生崩塌。以后崩塌逐渐加剧,大有不将葫芦形半岛冲完、冲直便不肯罢休之势。到了1931年,崩势逼近镇区。人们眼睁睁看着大块大块的江岸崩入江中;整座整座的房屋、桥梁、庙宇、古塔被江水吞没;整条整条的街道,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那惊涛裂岸、土崩瓦析、母呼儿嚎、求救无门的惨景,至今回忆起来,笔者仍觉余悸在心,不忍回首!值得敬佩的是,情势如此惨烈,簰洲人民始终不肯远离这个浸透了自己血汗的沃土,跟江水开展了长期的韧性搏斗!房屋临江了,来得及拆就拆,转盖在镇子的尾后;再临江,再拆,再盖……直到1962年,共崩塌了二十五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拆迁和崩毁房屋八千多座(幢)。此岸崩塌,彼岸委积,原先那座古老的簰洲镇址已被抛到江对岸了,而这个顽强的集镇却像金蝉蜕壳似的,一直保持着临江而立的姿态。
崩塌的灾难与地震无异,它像一个看不见的幽灵跟在簰洲人的背后,酿造恐怖,摧毁生机,破坏安宁,甚至制造死亡。但簰洲人并不一味退让,更不听天由命,早在1935年由镇人汪世鎏首先倡议,申请当局拨款,建矶护岸。虽然当局也派人勘测,并开始施工。但由于洪水成灾,专款挪用、芦沟桥事变、日寇侵华等原因,致使建矶工程趋于流产。1946年,汪世鎏及县长刘绍安等再兴此议,但当局以“簰洲乃一隅之地”为由,一推了事。直到1962年,簰洲人的夙愿才得以实现。人民政府成立了护岸机构,民办公助,各方集资。抛石护岸,砌坦保堤。到1985年,仅采用的石块即达256,000立方米。据说嘉鱼县近郊一座7里长的马鞍山的大部分石头,都投放到簰洲镇岸边了。由于扼制了崩塌,加固了堤防,人口递增了,街道增多了,经济发展了。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新兴的、繁荣的簰洲镇更加英姿勃发地屹立在古沙阳洲的江岸上。
也许读者要质疑:既然长江在此绕那么大个弯子,使水程徒然增加110华里,何不在它的葫芦口处凿开一条新航道,让江水顺性直流,岂不省事?是的,这样的设想,早在孙中山先生的国民政府就曾经计议过,解放以后,也有人再兴此议。但这么一来,江水直奔而下,就会使武汉的水位上升(据估计将升高1米),其后果是令人担忧的。特别是遇上大水之年,如果让高洪峰毫无节制地顺江而下,武汉市的防洪形势将更加严峻,而且大桥也将增受更大的冲力。所以,长江在武汉上游绕个大弯所形成的“曲流”,实在是南岭残丘的一大功劳,它无异给大江安了一个“缓冲装置”,经过“簰洲曲流”的制约、调节,汹涌难驯的江水才会心平气和地流经武汉。当地有两句民谣说得好:“绕过小小簰洲弯,武汉水低三尺三。”也只有如此,簰洲人在70多年间所作的艰苦搏斗和巨大牺牲才算没有白费。它扼制了崩塌,其实是加固了这个“缓冲装置”。既保存了自己,又保卫了大武汉。所以,我们把“簰洲曲流”比作大江的“缓冲装置”,是符合实际的说明;把解洲镇和解洲人比作武汉事实上的“安全卫士”,也就不会有“附会”之嫌了。
当一年一度江汛到来之际,在武汉长江上游75公里处,有一个无言的卫士在默默保卫着大武汉的安全①。这个卫士是谁?就是嘉鱼县的簰洲镇和它那有名的“簰洲曲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簰洲湾”。
为了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些,让我们打开三百五十万分之一的湖北分省图,只要您把视线从武汉市沿长江向西南移动大约一指宽的位置,就能看见长江在这里绕了个大弯。在弯子里,有一座很繁荣的集镇叫簰洲镇,也就是郭沫若先生在他的《洪波曲》中提到过的“簰洲——在地图上长江大转弯的那个地方。”②也许您要问:这长江大转弯跟武汉卫士有什么关系呢?“武汉卫士”又是怎么回事呢?好,现在就让我从头道来。
在古代,脾洲地区本不像现在这个葫芦形状的。据《禹贡》版图载,它是作为一座无名沙洲“存在于长江之中”的。到了汉代,它才有了正式命名:沙阳洲。 当时,这沙阳洲把长江分为南、北两条江流。到了晋初,南江北移,由于古老南岭残丘的抵制作用,迫使江水转向西流30华里,旋与东荆河汇合而转向北流,后又由北而转向东南,绕过整个沙阳洲回到与原南江航道相平行的位置。后经历代河道变迁,特别是宋代修筑堤防以后,江流曰趋稳定。到了民国初年,合镇垸大堤竣工,簰洲与老官地带相连,原先航道残留的決套完全淤成陆地,便形成了现今江流的葫芦形的半岛地势,而长江呢,就形成了这一段环形套似的“簰洲曲流”。
是的,在这一千多年的河道变迁中,南岭残丘是胜利者。为了不让喧嚣的江水破坏它宁静的环境,它成功地将长江扭曲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性情耿直而暴躁的大江,岂肯绕着弯儿多走110华里的冤枉路?于是它满怀怨愤地日夜冲击那弯弓似的江岸,而簰洲镇恰好首当其冲。
至于簰洲镇是怎样在这个葫芦形半岛上发展起来的,说来话就长了,这里只能作一个简略的说明。据载,簰洲地区属古沙阳洲,是古云梦泽冲积平原的一部分。此地气候四季分明,土地十分肥沃,先秦时就有人来此开垦,汉初便开始形成商埠,明初已成为邻近各县及川湘两省的贸易市场及各类物资的集散中心。簰洲本来地处长江南岸,因有30里西流水而成了北岸。岸陡水深,北风难袭,是难得的避风良港,往来船只都喜欢在此停靠,特别是从四川、湖南下来的竹簰、木筏停靠最多。因此,到了元代人们便称之为“脾洲”。后经明清两代的经营、发展,到了清末民初,簰洲已成为一座相当繁荣的商埠了。它不仅拥有48条街道,4万多居民,仅槽房、榨房就有100多家,各种商行、商店近千家。沿江看去,但见高樯林立,长簿蜿蜒,汽笛啸江,人声催浪,真可谓工商繁盛,各业俱全,车载船运,水陆两旺,难怪一时享有“小汉口”之美誉!
谁能想到、谁能想到啊!远从明代正德以来,一种不祥的阴云开始笼罩簿洲。因其地属长江冲积平原,地层大量含沙,江涛冲刷,坡岸洗空,开始发生崩塌。以后崩塌逐渐加剧,大有不将葫芦形半岛冲完、冲直便不肯罢休之势。到了1931年,崩势逼近镇区。人们眼睁睁看着大块大块的江岸崩入江中;整座整座的房屋、桥梁、庙宇、古塔被江水吞没;整条整条的街道,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那惊涛裂岸、土崩瓦析、母呼儿嚎、求救无门的惨景,至今回忆起来,笔者仍觉余悸在心,不忍回首!值得敬佩的是,情势如此惨烈,脾洲人民始终不肯远离这个浸透了自己血汗的沃土,跟江水开展了长期的韧性搏斗!房屋临江了,来得及拆就拆,转盖在镇子的尾后;再临江,再拆,再盖……直到1962年,共崩塌了二十五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拆迁和崩毁房屋八千多座(幢)。此岸崩塌,彼岸委积,原先那座古老的脾洲镇址已被抛到江对岸了,而这个顽强的集镇却像金蝉蜕壳似的,一直保持着临江而立的姿态。
崩塌的灾难与地震无异,它像一个看不见的幽灵跟在簰洲人的背后,酿造恐怖,摧毁生机,破坏安宁,甚至制造死亡。但簰洲人并不一味退让,更不听天由命,早在1935年由镇人汪世鎏首先倡议,申请当局拨款,建矶护岸。虽然当局也派人勘测,并开始施工。但由于洪水成灾,专款挪用、芦沟桥事变、日寇侵华等原因,致使建矶工程趋于流产。1946年,汪世鎏及县长刘绍安等再兴此议,但当局以“簰洲乃一隅之地”为由,一推了事。直到1962年,簰洲人的夙愿才得以实现。人民政府成立了护岸机构,民办公助,各方集资。抛石护岸,砌坦保堤。到1985年,仅采用的石块即达256,000立方米。据说嘉鱼县近郊一座7里长的马鞍山的大部分石头,都投放到簰洲镇岸边了。由于扼制了崩塌,加固了堤防,人口递增了,街道增多了,经济发展了。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新兴的、繁荣的簰洲镇更加英姿勃发地屹立在古沙阳洲的江岸上。
也许读者要质疑:既然长江在此绕那么大个弯子,使水程徒然增加110华里,何不在它的葫芦口处凿开一条新航道,让江水顺性直流,岂不省事?是的,这样的设想,早在孙中山先生的国民政府就曾经计议过,解放以后,也有人再兴此议。但这么一来,江水直奔而下,就会使武汉的水位上升(据估计将升高1米),其后果是令人担忧的。特别是遇上大水之年,如果让高洪峰毫无节制地顺江而下,武汉市的防洪形势将更加严峻,而且大桥也将增受更大的冲力。所以,长江在武汉上游绕个大弯所形成的“曲流”,实在是南岭残丘的一大功劳,它无异给大江安了一个“缓冲装置”,经过“脾洲曲流”的制约、调节,汹涌难驯的江水才会心平气和地流经武汉。当地有两句民谣说得好:“绕过小小簰洲弯,武汉水低三尺三。”也只有如此,簰洲人在70多年间所作的艰苦搏斗和巨大牺牲才算没有白费。它扼制了崩塌,其实是加固了这个“缓冲装置”。既保存了自己,又保卫了大武汉。所以,我们把“脾洲曲流”比作大江的“缓冲装置”,是符合实际的说明;把解洲镇和解洲人比作武汉事实上的“安全卫士”,也就不会有“附会”之嫌了。(陈贤林)
此文选自由嘉鱼县文化和旅游局、嘉鱼县作家协会联合编著的《南有嘉鱼》丛书。该书已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发行。
来源:南有嘉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