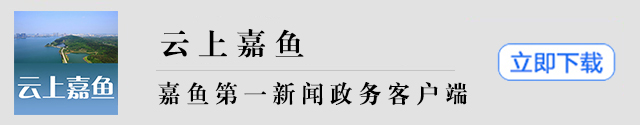一夜春雨,打湿了窗台,打湿了夜梦。我想回一次故乡,因为我梦见了自家老屋旁的那棵香樟树。
经过春雨沐浴洗礼,天纯净,气清新,阳光柔照,心情畅爽。出了城门,就是一片葱茏沃野,生机盎然。嘉陆公路沿线,黄灿灿的油菜花绵延数里,扑鼻的芳香,引得蜂飞蝶舞。成垄的麦苗挂着透亮的玲珑水珠,在和煦的微风中泛起层层绿波。一家家果园、一片片花圃,无不枝繁叶茂,姹紫嫣红。一家家农庄、一片片基地,无不人流如织,一片繁忙。
车在环形乡路上蜿蜒行进,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昨夜的梦境:我家乡老屋的邻居、满头白发的想生婶连声高喊:“爱子(我的乳名),你快回舒家嘴一趟,你栽的香樟树不见了!你栽的香樟树不见了!”我听见后,疯子一般冲出家门,慌乱中摔倒在楼道里,从10多层高一顺滚下楼底,嘴里大喊着:“我的香樟树!我的香樟树!”
梦中猛然惊醒后,却见房间的灯开着,年迈的妈妈站在我的床前,一脸惊愕:“爱子,你是不是做梦了?爱子,你是不是吓着了?”
“妈,我想回趟舒家嘴。”我拉着妈妈的手:“我想去看看老屋旁的那棵香樟树。”
“哎,不晓得它还在不在呢?早就听说有人要想它的心事,打它的主意。”
我也怅然若失起来:“是啊,那棵香樟树还在不在呢?”
这不是一棵普通的香樟树。
六岁那年,家里盖了三间土砖房。爸爸就寻思着要在房前屋后栽上些树,九岁的哥哥不知道从何处弄来些桃树李树苗,成排栽在了后院。爸爸高兴地说:“好,过不了几年,我们家就有吃不完的桃子李子了!”并给哥哥专门下了碗荷包蛋面条以示奖赏。而我也不甘示弱,用把小土铲从对面山上挖来一棵小香樟树苗,独自栽到了屋旁,还喊来爸爸:“我也栽树了,我也要吃荷包蛋面!”爸爸漫不经心地说:“栽香樟树没什么用,值不上吃荷包蛋面。”说着就想把它拔掉。还是妈妈打圆场:“栽了就栽了,总还能遮遮荫!”我终究没有得到所想要的荷包蛋面。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物质利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是多么重要,甚至会淡化亲情而产生些许不公。
不知不觉几年过去了,哥哥栽在后院的桃李全部挂果成熟,每当他递一个桃子李子家人手上时,都不忘说“尝尝我种的”,家人总是一致地说“好甜好甜”。那份自豪和荣耀,像一个胜利归来的战士般神气活现。而我的那棵香樟树虽也长得亭亭玉立,但没有谁注意它,更没有谁夸赞我。我第二次感受到,一个人的地位高低和价值大小,取决于你给别人带来什么、带来多少。
然而,一场“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到来了。哥哥栽的满院桃李因为会带来副业收入而遭殃,全部被拦腰砍断。看着散落满地将熟未熟的果子,哥哥哭红了眼,爸爸咬断了牙。妈妈只能怯生生地看着那群人的背影离去,然后拉起我的手抱着屋旁的那棵幸免于难的香樟树,久久不放、默默无语。
又是几年过去了,我高中毕业了,因多种无法表述的原因考试失常,黯然落榜,回到了村里务农。香樟树和我一样,长得更高了,长得更壮了,像一个卫士般守护着我家那三间风雨飘摇的土屋。那个落寞失望的夏夜,我靠着香樟树,看流萤纷飞,听樟叶絮语,年轻的心中筹划着并不明确的未来。
爸爸到一个单位“亦工亦农”了,哥哥在村里当民兵连长了,我和妈妈守在家里,一起种着十来亩责任田。生产劳作之余,我报考了文学创作函授,埋头看书写作,做起了美好的“作家梦”。不久,为了搞点活钱贴补家用,我决定到一家采石企业做临时工。离开家的那天晚上,妈妈与我坐在香樟树下的石凳上,她不停地叮嘱着这,提醒着那。忽然,一片樟叶飘落在我的头上,掉在我的胸前。许是香樟树舍不得我离开,我顺手把那枚樟树叶拾起,当作书签,带在身边。
对于无比瘦弱的我来说,采石的工作异常繁重,但心中有家的担当,我不觉得苦。工休的日子无比空虚,但心中有文学为伴,我不觉得闷。青春总会逢花事,我和一个女孩走近了。一年多来,漆家山的林荫路见证了我们的欢笑,家乡屋旁的香樟树见证了我们的甜蜜。
但是,一把世俗的无情刀,斩断了我们的相思,我们的牵挂,一个凄风冷雨的秋夜,一场泣血零泪的离别,我把因家境而导致的情殇刻在了香樟树上,把一份不甘和期待寄托给了未来:“等着我!”
人往往无法主宰内心和未来,人生注定是一场情节曲折的连续剧。“等着我”的却是命运的重新选择、情感的重新定位、生活的重新起步。我通过公开招考当了记者,而后当了干部,再后成了作家。我经过热烈追求娶了妻子,而后生了孩子,再后买了房子。我离开了家乡,住进了城中,和妈妈相见的时候越来越少,在香樟树下流连的时间越来越短。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因为父母没有能力进行修缮,家里的土砖屋出现了严重倾斜,多亏了香樟树那遒劲的树枝支撑着,密匝的树叶遮挡着,才保持了它的安然。我们兄妹几个相继成人,也先后在城里安家,便把渐趋年迈的父母接到了身边,只剩下香樟树和老土屋相依相伴。在一个狂风恶雨之夜,老土屋卷带着几杆樟树枝,轰然坍塌成了一片废墟。从此,香樟树孤独地挺立在村子前,虽然没有了主人,却也依旧四季常青。有搞旅游的人说,这是舒家嘴的一道地标风景。也有采风的文友说,这是我爱子留在舒家嘴的一份乡情记忆。
自此,我们回舒家嘴变得更少了,偶尔的回乡清明祭祖,也是匆匆上山匆匆下山,甚至都很少到村子中去,更别说见到香樟树了。期间偶尔传说过有人要挖了香樟树修晒场,砍了香樟树盖新房,伐了香樟树打水井,多亏了想生婶的仗义阻止才没有如愿。作为长年累月在这棵香樟树下歇荫乘凉、拉扯家常的老邻居,想生婶对香樟树的那份情感或许并不亚于我和家人。
这不,又是想生婶在梦中的“呼唤”,让我必须回一次故乡,见一眼我栽下的香樟树。车子刚进村子的路口,我就见到了满头银发、腰身佝偻的想生婶。算起来,我都有十多年没有见过她老人家了,当我一把拉住她的手时,还是感到那么亲切和温暖。原来,我给堂叔打的电话让想生婶知晓了,她是特地来村口等我接我的。
“婶,您老的身体和精神还好吧?”我抬高了嗓音与有些耳疾的想生婶打着招呼。
想生婶一面用干瘦的手摸着我:“爱子你变了,身子发胖了,皮肤变白了,走路不急了,声音也不像了。”
“他离开村子这么多年,难得见到我们一面,确实是有蛮大变化。”闻讯而来的堂叔也跟着说。
“冇变冇变,我还是原来的爱子。”我多少有些内疚和尴尬,连忙回应着他们:“还是昨天夜里梦见想生婶提醒我,所以今天专门回来看看那棵香樟树的!”
一时,大家都脸色阴沉,默不作声了。
“想生婶,您老快说,香樟树怎么了?”我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想生婶怔怔地没有动,好一阵,一行老泪从浑浊的眼眶缓缓流出。“爱子,我对不住你,人老了,说话不中听了,我没有拦住那些老板,香樟树被人家卖到城里去了……”说完,想生婶竟然抽泣起来。
我一时也头脑发木,说不出任何话来。继而拔腿就跑向我的老屋,却因为村子改造了,新建了不少房子,路也改道了而跑错了方向。当我找到老土屋时,只看到一个不大不小的土包上,长满了各种杂草和小树,那棵曾经倾注了我无数心血、带给我无数牵挂、承载我无数情感的香樟树——不见了!
记不清我在那儿呆立了多久。这时组长来了。“爱子,你总是不回,又没有把这棵树当回事,组里搞新农村改造,需要用钱,正好有个房地产老板看中了这棵树,我们一商量,就决定把它卖了,也算是你这吃国家饭的人为家乡做点公益、作点贡献!”
我茫然看着组长。我本可以说,这是我家的树,是我们家的私有财产,你们没有权力自作主张处置。我甚至想向组长说,新农村改造关我什么事、关我家什么事、关香樟树什么事?但不知何故,我真的说不出来。我沿着新修的村路漫无目的走着,我想找找刻在心中和脑际的过去记忆,但是,一切是新的,仿佛又是旧的,让人辨不清、说不明。那满山的松杉和檀木不见了,却新栽了满坡的油茶和枇杷;那弯弯的荷塘、清澈的河水不见了,却挖成了鱼池、放养了龙虾;那宽敞热闹的舒家祠堂不见了,变成了垃圾收集中转站;村中那玩龙灯、听楚剧的戏台子不见了,变成了闲时的麻将馆、老年人晒太阳的集聚地……这一切,不知道是不是在进步,是不是在发展,是不是一种希望和出路?我毕竟是舒家嘴走出去的人,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铭刻在脑海里,每一个人无论是亲是疏都牢记在心坎上,因此,这里的改造和发展不能说完全与我无关,我们注定不可能脱离故乡、忘记家乡!所以村子的一切就关自己的事、关自家的事、也关香樟树的事。既然组长赋予香樟树如此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我多少缓解了一下内心的惆怅和失落。
现在我只想搞清楚这棵香樟树卖到了哪里,我好歹要去见它一面。组长是个直爽人,给了我一个确切的地址和联系人。我按图索骥找到那家新做的楼盘小区,经过物业管理员找到了我家那棵香樟树,我彻底惊呆了:在这高楼林立、亭台杂错、曲径通幽、花团锦簇的小区中,我家的香樟树和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其他香樟树成排而立,高高的树干被拦腰锯断,只剩下丈许高的硕大树柱,留下的几杆弯斜的树枝长出了鲜嫩的枝叶,树底周围砌了一道贴花护墙,其中铺种了名贵矮竿草皮,间植了鲜艳的盆栽小花。这哪里还是我家屋旁那棵坚挺刚劲、古朴粗犷的香樟树?俨然像一个穿着盛装、满头油光、志得意满的都市商务白领!
我忐忑地走近香樟树,试图在它的身上寻找曾经的刀刻,但始终没有看到“等着我”三个字。多年的生长和发育,早已掩没了这份铭刻。我再次无语,陷入了沉思:莫非是香樟树没有等到我回到它身边,它失望了、它伤心了?莫非是我离开家乡、走进城市,已经变得不是原来的我,它也在随波逐流以寻求改变?莫非香樟树在变革中的乡村失去了价值,只有在城市的花园中才得以真正体现?
我无法找到其中答案,突然心生愧疚和彻悟:既然是自己缺乏对家乡、对乡亲、对恋人的坚守和初心,没有真正践行“等着我”的诺言,又何必在意香樟树的脱离故土、摇身一变?别等我们失去了才觉后悔、离开了才知珍惜。于是,我暗暗给自己一个约定:每年至少回一次家乡,看一看那里的山山水水,闻一闻那里的泥土气息,亲一亲乡亲父老,做一做农活家务,把乡情蒸煮进家常便饭里,把乡音吹奏进泥哨叶笛中,把乡愁穿戴在蓑衣斗笠上,把乡思揉捏在糍粑发糕间。虽然进了城、变了形的香樟树不再“等着我”,但那里还有想生婶和堂叔“等着我”!还有千年的根、万代的本“等着我”!
最后我又在想:假如我们的政府和部门多为乡村建设投点资、出点力,我家屋旁的那棵香樟树是不是就不会被卖掉,反倒会成为乡村的一道靓丽风景?假如我们现在一起努力,把乡村建设得像城市一样漂亮,我家屋旁的那棵香樟树还会不会再回到故乡?
香樟树不会说话,无法回答。只能想象在它的内心,或许也有一种“等着我”的渴望与呼唤!(舒爱民)
此文选自由嘉鱼县文化和旅游局、嘉鱼县作家协会联合编著的《南有嘉鱼》丛书。该书已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发行。
来源:南有嘉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