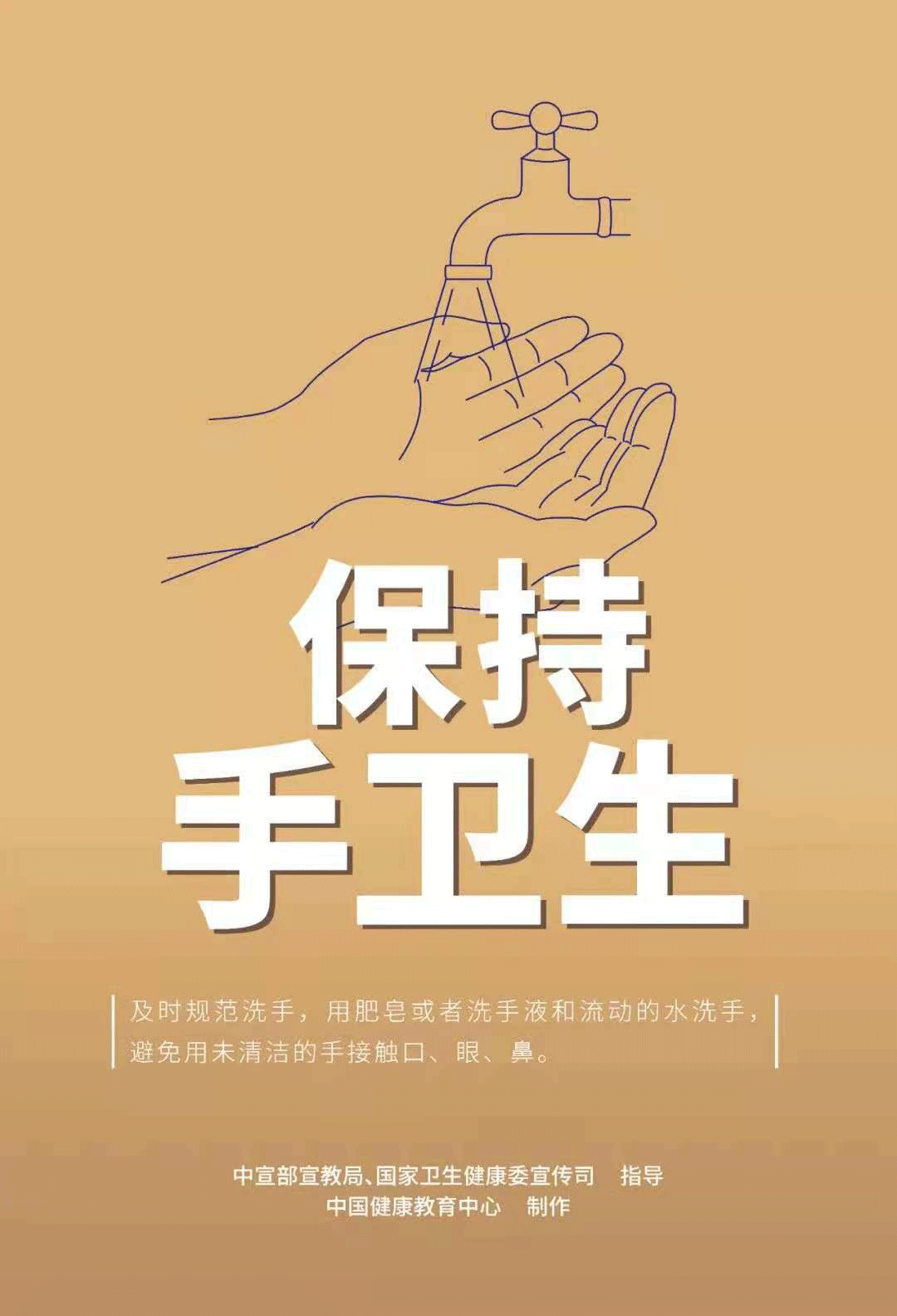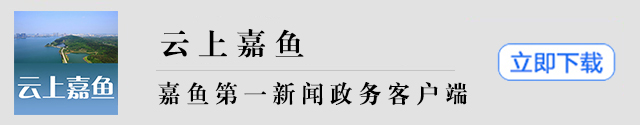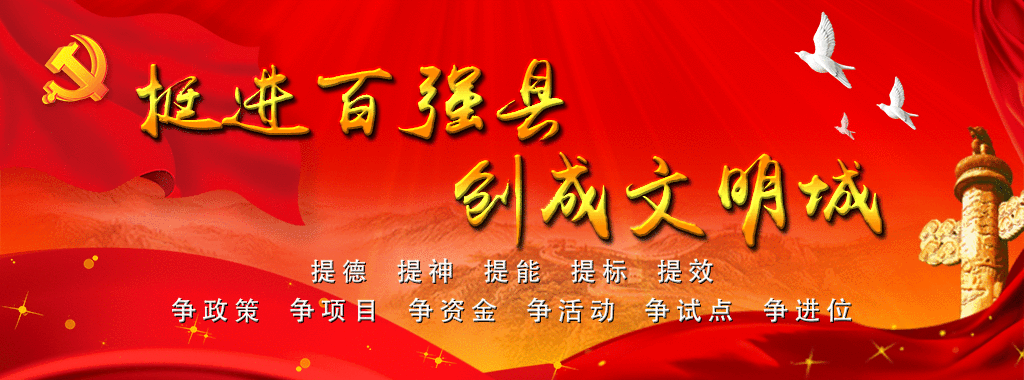
每当捧起清凉的自来水,不由想起我们乡下那口位于李树林下露天的水井。
小的时候,爷爷说,我们村的水井原先是在村子下头的一口池塘边。因水质不够好,夏季的时候稍微有点旱情就会断水。后来(在我出生前四十年),在距离我家老屋十来米远的李树林子里,爷爷发现了又一水源,就号召村里的劳力在果树林里的泉口边挖成了一口新井。
这口井,呈心形,有七八个平方,深六米。井的顶端是一棵大李树,左右两边生长着一种春季能开出漂亮花朵的刺藤,两边的井弦向下倾斜,与下边一块平平整整的青石板衔接,这块三米多长一米多宽的青石光光顺顺的,受到了全村人的青睐。
井水清冽甘美,冬暖夏凉。冬天里,用井水洗衣服不觉冷手;大热天,井水又凉爽爽的,如饮甘露。爷爷说这是一股地地道道的山泉水,再大的干旱,也没见干涸过。平日里,井水也不会漫过青石板,水面距离井面始终有四五寸,就是我们小孩去井里打水,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们奇怪,井水为什么不会漫过青石呢?后来才知道那可是爷爷的智慧。爷爷在水井右下角的石板下面凿开了一道缺口,多余的井水就从这道缺口里流进笔直向下的水沟了。水井往下二十几米远,是一方藕塘,每次大雨(老人说是〞动了山脉〞)过后,这条水沟里的水就会叮叮咚咚,特别欢快地流向藕塘,因而这股活水也润泽着藕塘。到了夏天,满塘的荷花在绿意里悄悄地绽放,给人一朵又一朵的惊艳。
我和井最亲密的时候,是李子成熟的时节。几十棵的李树林子,挂起果来,金灿灿、红彤彤的,实在是诱人。果子多了,自家人吃不完。我就是从家里拿来一个盆子,从井里舀上来一盆清清凉凉的水,从树上摘下又大又亮的李子,放进盆里,骨骨碌碌地洗一洗,然后呼朋唤友来品尝。小同伴们叽叽喳喳、热闹轰抢,争相抓吃。于是享用李子大餐的时刻就开始了。小同伴们的吃相很不斯文,抓起李子就往嘴里攥,贪婪地咬着嚼着。熟透的李子红红的,在嘴里有如密饯一样甜,而金黄金黃的李子脆甜中还带点酸。李子多的是,我和小同伴们都是吃得撑得圆溜溜的肚子才肯罢休。
李子成熟的时节,大人来井里挑水也都是笑嘻嘻的。他(她)们总是先摘一些红透的李子塞满口袋,再回头捡起扁担挑水回家。还边走还边吃着李子,没留神时,水桶撞到李树上,水会泼洒出来,溅到地上。
为了不让大人摘,爷爷就会搬上一把靠椅坐到李树下,闲散地抽着烟锅。担水的大人和过路的人都很识趣,知道他是在守李子。但我不怕,当李子少的时候,稀稀朗朗的几个挂在树顶上,我就得爬上李树,边摘边吃。一顿狼吞虎咽,我懒懒地坐在树杈上发呆,视线向井水游移,不知灵感从何处而来,那次,我发觉树下的那口井像眼睛,温情款款,清纯灵秀的眼睛!
如今,那个见证我生命根源的小村已经不在了,李树林子和井也都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拔地而起的化工厂。母亲说,化工厂特别兴旺就因沾了那口风水宝地的灵气。当然,我不会十分认同母亲的说法。在我心里,那股滋养了祖孙几代人的井水一直活着,与我血脉相通。每回靠扰这片土地,想起儿时的村庄,李树林子里的那口井,总会率先占领思乡的源头,那股涓涓的甘泉就会穿过林荫,携着花香鸟鸣,进驻我的心田。(蔡安心)
此文选自由嘉鱼县文化和旅游局、嘉鱼县作家协会联合编著的《南有嘉鱼》丛书。该书已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发行。
来源:南有嘉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