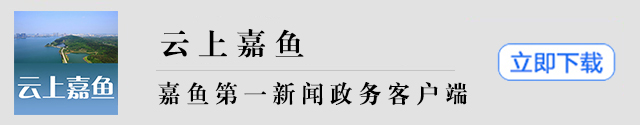在柳絮漫天飘舞的五月,我回乡探望年迈的父亲和母亲。母亲说,你来的正好,和我一块回村里看看你二姑吧。我听了满心的喜悦,差不多有三五年没回村了吧,我是多么的想念那座满载着我美好童年时光的村庄啊!
早在二十多年前,父亲将村里一片无人问津的沼泽地改为鱼塘,便与母亲搬到鱼塘边居住,先是搭建一座草棚,后来建了两间低矮的瓦屋,再后来修建了三间大瓦房,另加厨房、猪圈,还有鸡舍,算是彻底的搬离了村庄。继父亲之后,又有几家将此处的稻田改为鱼塘,也在鱼塘边建了房舍,这里便逐渐形成了一座小小的“渔村”。紧邻小“渔村”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水泥公路,便于众多鱼贩子的车辆进出。公路的左边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右边是波光粼粼的鱼塘,视野开阔,空气清新,静谧却并不孤单。难怪一直在家种地的二弟五年前也搬离了村庄,来此和父母一起居住。“渔村”离我们的村庄大约五里地的距离,自二弟一家搬至此处,村里再也没有我至亲的人,所以一晃就有多少年没有回去了。
哦,那座位于长江之滨的美丽村庄,那片生我养我的芬芳土地,那“碧天莲叶无穷尽,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莲花湖,那潺潺流淌的村前小河,可还是初见的模样?
走进村庄,听不见流水声,听不见狗叫,甚至听不见鸟鸣,只有午后的阳光温暖地抚摸着这片土地。阳光落在村前的那条小河上,小河是干涸的,曾经清澈的河水不知流向了哪里;阳光落在房舍上,不见袅袅的炊烟,不见筑巢的春燕,但见破败不堪的墙垣和一丛丛疯长的野草,但见紧闭的木门和门上锈迹斑斑的大锁;阳光落在树木上,不见杨柳依依,不见翠绿欲滴,不见紫葡萄似的桑葚,印有年轮的大树已被砍伐,光秃秃的树兜旁生发出一些杂乱的新枝,也有一些新插的白杨,歪歪斜斜,像一个个失去营养的孩子,没精打采的;阳光落在村中的水泥路上,路面时不时摇晃着单薄的树影,也摇晃着我脑海里那些零碎的记忆。这条路贯穿整个村庄,三十年前,父亲是我们村的队长,他带领乡亲们拖石头,运沙土,和水泥,干得热火朝天,修了这条水泥路,和家家户户门前的水泥禾场。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遍村村落落,责任到田到户才刚刚开始,乡间随处可见的是崎岖的泥泞之路,队里的打谷场上堆满了各家各户的稻谷,大家伙排着队日夜打场。所以这条水泥路和禾场的修建成了当时的一大壮举,甚至轰动了当时的镇政府,使父亲狠狠地“火”了一把。现如今,对于七十多岁的父亲来说,这条路已成为他人生中的一座充满无限荣光的里程碑。哪怕这条路已修复多次,只留有当年路基的痕迹。
从村头往里走,差不多有十户人家的房子是“人去楼空”。我问母亲,这些人家都去了哪里。母亲说,他们都在县城里买了房,都富裕了。我说,富裕了就一定要住在城里吗,这里的空气多好。母亲说,如今在城里买房是一件多么有面子的事,哪个讲空气的好坏。说话间就到了二姑家,二姑家处于村庄的“繁华地带”,左右连续七八家都有人烟。二姑大病初愈,正躺在门前的一把躺椅上晒太阳,她的旁边围坐着五六个乡亲,姑父正和他们聊得特别起劲。见到我,二姑格外的高兴,起来要给我们倒茶,我按住了她。姑父连忙收起话匣子,开着他的小三轮电动车到集市上去买菜。我和在坐的乡亲们一一打招呼,他们大多是我的长辈。我还记得他们,他们有的却忘记了我。
春生大伯已八十多岁,眼睛不好,我叫他的时候,他瞅了半天也没把我认出来。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都接了媳妇添了孙,无暇顾及他,二儿子一家人在深圳打工,接他去,他不愿意。他宁愿孤单一人守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他说,金窝银窝比不上咱这穷窝。长珍大娘矮矮的个头,七十多了,看上去身子骨还十分的硬朗,她亲昵地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我一番,说,这姑娘还是跟以前一个样哦,没有变呀。她的五个儿女都在外边,家里只剩她和老伴,却依旧种着自家将近二十亩的责任田。听母亲讲,长珍大娘小时候可是地主家的千金小姐,她家的土地在土改时充了公,她的父母被批斗,最后都自缢身亡。也许因经历过这样的人生沧桑,她惜土如金,哪怕广种薄收,也不愿意把地租给别人。想兰算是留守村庄的最年轻的女人了,长我两岁,却是我的小学同学,见到我,显得格外的亲昵。她人很憨直,长得胖而黑,二十年前嫁给了我们村相貌堂堂脑袋瓜却有些毛病的明哥,生了三个女孩,大女儿智商有问题。那些年,村里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她不曾走出过村子,带着三个孩子,一门心思在家种地。现在,她的二女儿已出嫁,婆家家境还比较殷实,三女儿初中毕业就去了广东打工,每月都往家里寄钱。她说,我这一辈子就带着这个傻姑娘耗在这里了。她的那个傻姑娘站在她身边,长得牛高马大,拽着她的衣袖,乐呵呵地傻笑。看到想兰已显苍老的面容,一种苦涩的滋味涌上心头。
村里算得上最有头脑的人应该是我的堂哥红林了,他就住在二姑家的隔壁,这时间正端着饭碗坐在人群中。他告诉我,因为忙着村里土地流转的事,所以才吃上午饭。五十多岁的红林哥年轻时是村里有名的“懒汉”,守着自家的几亩薄田过日子,家境不富裕,却也落得个舒舒服服。他喜欢看书,特别是《今古传奇》和《聊斋志异》,所谓“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的他,冬天坐在火堆旁,夏天坐在大树下,口若悬河地给村民讲一些奇闻怪事,特别会讲鬼故事,我的堂嫂就是当年听他讲鬼故事,一时害怕钻到他的怀里,后来便嫁给了他。二姑说,你红林哥算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他女儿在大连打工,嫁到当地一户好人家,儿子在城里一家车行做修理工,都是自力更生,哪个都没让他操心。红林哥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到,二姑这样说比骂我都还要重呀。
现在的红林哥是我们村的小组长,除了自家的几亩地,还承包了好几十亩水田。他告诉我说,村里原来有五十多户人家,现如今只剩下十几户,都是些老弱病残的人,特别是一些老人无人照顾,去年夏天竹青叔突发脑溢血死在家中,两天后才被人发现,他儿子一家都在北京打工,等他们赶回来,尸体都着了气味,真是蛮伤心啊。一旁的春生大伯插了一句,“我不知哪一天也和他一样没有声响地去了阴间啊”。二姑说,不会,你大儿子一家就在县城,离得近呢,一说不行了就去他那里,哪像竹青只有一个儿子呀。红林哥接过话,继续说到,前几天有外地的老板来村里,说要承包土地,村里的老人们不同意,村里的干部十分的着急。唉,你说也是,我们村的莲花湖被填平,栽上了白杨;村前的小河被淤塞,只剩下堆满垃圾的河床;年轻人都进了城,倘若地也没了,没准哪一天这村庄就不存在了……
听完红林哥的一席话,太阳已渐渐偏西,我浑身上下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心间平添一种无言的忧郁。姑父已做好一桌丰盛的饭菜,吃过晚饭,二姑执意留我,我还是逃也似的离开了村庄,和母亲回到了“渔村”。我害怕村庄里黑夜的寂寥,我害怕听到更多悲伤的故事,我害怕时光会慢慢蚕食掉那些关于故乡关于村庄的美好记忆。
再见了,我曾经美丽可爱的村庄。多年以后,我还会回到这里,哪怕你已被历史的烟云所淹没!哪怕你已被众多的人们所遗忘!因为我的爱早已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许爱琼)
此文选自由嘉鱼县文化和旅游局、嘉鱼县作家协会联合编著的《南有嘉鱼》丛书。该书已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发行。
来源:南有嘉鱼


在柳絮漫天飘舞的五月,我回乡探望年迈的父亲和母亲。母亲说,你来的正好,和我一块回村里看看你二姑吧。我听了满心的喜悦,差不多有三五年没回村了吧,我是多么的想念那座满载着我美好童年时光的村庄啊!
早在二十多年前,父亲将村里一片无人问津的沼泽地改为鱼塘,便与母亲搬到鱼塘边居住,先是搭建一座草棚,后来建了两间低矮的瓦屋,再后来修建了三间大瓦房,另加厨房、猪圈,还有鸡舍,算是彻底的搬离了村庄。继父亲之后,又有几家将此处的稻田改为鱼塘,也在鱼塘边建了房舍,这里便逐渐形成了一座小小的“渔村”。紧邻小“渔村”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水泥公路,便于众多鱼贩子的车辆进出。公路的左边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右边是波光粼粼的鱼塘,视野开阔,空气清新,静谧却并不孤单。难怪一直在家种地的二弟五年前也搬离了村庄,来此和父母一起居住。“渔村”离我们的村庄大约五里地的距离,自二弟一家搬至此处,村里再也没有我至亲的人,所以一晃就有多少年没有回去了。
哦,那座位于长江之滨的美丽村庄,那片生我养我的芬芳土地,那“碧天莲叶无穷尽,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莲花湖,那潺潺流淌的村前小河,可还是初见的模样?
走进村庄,听不见流水声,听不见狗叫,甚至听不见鸟鸣,只有午后的阳光温暖地抚摸着这片土地。阳光落在村前的那条小河上,小河是干涸的,曾经清澈的河水不知流向了哪里;阳光落在房舍上,不见袅袅的炊烟,不见筑巢的春燕,但见破败不堪的墙垣和一丛丛疯长的野草,但见紧闭的木门和门上锈迹斑斑的大锁;阳光落在树木上,不见杨柳依依,不见翠绿欲滴,不见紫葡萄似的桑葚,印有年轮的大树已被砍伐,光秃秃的树兜旁生发出一些杂乱的新枝,也有一些新插的白杨,歪歪斜斜,像一个个失去营养的孩子,没精打采的;阳光落在村中的水泥路上,路面时不时摇晃着单薄的树影,也摇晃着我脑海里那些零碎的记忆。这条路贯穿整个村庄,三十年前,父亲是我们村的队长,他带领乡亲们拖石头,运沙土,和水泥,干得热火朝天,修了这条水泥路,和家家户户门前的水泥禾场。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遍村村落落,责任到田到户才刚刚开始,乡间随处可见的是崎岖的泥泞之路,队里的打谷场上堆满了各家各户的稻谷,大家伙排着队日夜打场。所以这条水泥路和禾场的修建成了当时的一大壮举,甚至轰动了当时的镇政府,使父亲狠狠地“火”了一把。现如今,对于七十多岁的父亲来说,这条路已成为他人生中的一座充满无限荣光的里程碑。哪怕这条路已修复多次,只留有当年路基的痕迹。
从村头往里走,差不多有十户人家的房子是“人去楼空”。我问母亲,这些人家都去了哪里。母亲说,他们都在县城里买了房,都富裕了。我说,富裕了就一定要住在城里吗,这里的空气多好。母亲说,如今在城里买房是一件多么有面子的事,哪个讲空气的好坏。说话间就到了二姑家,二姑家处于村庄的“繁华地带”,左右连续七八家都有人烟。二姑大病初愈,正躺在门前的一把躺椅上晒太阳,她的旁边围坐着五六个乡亲,姑父正和他们聊得特别起劲。见到我,二姑格外的高兴,起来要给我们倒茶,我按住了她。姑父连忙收起话匣子,开着他的小三轮电动车到集市上去买菜。我和在坐的乡亲们一一打招呼,他们大多是我的长辈。我还记得他们,他们有的却忘记了我。
春生大伯已八十多岁,眼睛不好,我叫他的时候,他瞅了半天也没把我认出来。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都接了媳妇添了孙,无暇顾及他,二儿子一家人在深圳打工,接他去,他不愿意。他宁愿孤单一人守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他说,金窝银窝比不上咱这穷窝。长珍大娘矮矮的个头,七十多了,看上去身子骨还十分的硬朗,她亲昵地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我一番,说,这姑娘还是跟以前一个样哦,没有变呀。她的五个儿女都在外边,家里只剩她和老伴,却依旧种着自家将近二十亩的责任田。听母亲讲,长珍大娘小时候可是地主家的千金小姐,她家的土地在土改时充了公,她的父母被批斗,最后都自缢身亡。也许因经历过这样的人生沧桑,她惜土如金,哪怕广种薄收,也不愿意把地租给别人。想兰算是留守村庄的最年轻的女人了,长我两岁,却是我的小学同学,见到我,显得格外的亲昵。她人很憨直,长得胖而黑,二十年前嫁给了我们村相貌堂堂脑袋瓜却有些毛病的明哥,生了三个女孩,大女儿智商有问题。那些年,村里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她不曾走出过村子,带着三个孩子,一门心思在家种地。现在,她的二女儿已出嫁,婆家家境还比较殷实,三女儿初中毕业就去了广东打工,每月都往家里寄钱。她说,我这一辈子就带着这个傻姑娘耗在这里了。她的那个傻姑娘站在她身边,长得牛高马大,拽着她的衣袖,乐呵呵地傻笑。看到想兰已显苍老的面容,一种苦涩的滋味涌上心头。
村里算得上最有头脑的人应该是我的堂哥红林了,他就住在二姑家的隔壁,这时间正端着饭碗坐在人群中。他告诉我,因为忙着村里土地流转的事,所以才吃上午饭。五十多岁的红林哥年轻时是村里有名的“懒汉”,守着自家的几亩薄田过日子,家境不富裕,却也落得个舒舒服服。他喜欢看书,特别是《今古传奇》和《聊斋志异》,所谓“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的他,冬天坐在火堆旁,夏天坐在大树下,口若悬河地给村民讲一些奇闻怪事,特别会讲鬼故事,我的堂嫂就是当年听他讲鬼故事,一时害怕钻到他的怀里,后来便嫁给了他。二姑说,你红林哥算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他女儿在大连打工,嫁到当地一户好人家,儿子在城里一家车行做修理工,都是自力更生,哪个都没让他操心。红林哥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到,二姑这样说比骂我都还要重呀。
现在的红林哥是我们村的小组长,除了自家的几亩地,还承包了好几十亩水田。他告诉我说,村里原来有五十多户人家,现如今只剩下十几户,都是些老弱病残的人,特别是一些老人无人照顾,去年夏天竹青叔突发脑溢血死在家中,两天后才被人发现,他儿子一家都在北京打工,等他们赶回来,尸体都着了气味,真是蛮伤心啊。一旁的春生大伯插了一句,“我不知哪一天也和他一样没有声响地去了阴间啊”。二姑说,不会,你大儿子一家就在县城,离得近呢,一说不行了就去他那里,哪像竹青只有一个儿子呀。红林哥接过话,继续说到,前几天有外地的老板来村里,说要承包土地,村里的老人们不同意,村里的干部十分的着急。唉,你说也是,我们村的莲花湖被填平,栽上了白杨;村前的小河被淤塞,只剩下堆满垃圾的河床;年轻人都进了城,倘若地也没了,没准哪一天这村庄就不存在了……
听完红林哥的一席话,太阳已渐渐偏西,我浑身上下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心间平添一种无言的忧郁。姑父已做好一桌丰盛的饭菜,吃过晚饭,二姑执意留我,我还是逃也似的离开了村庄,和母亲回到了“渔村”。我害怕村庄里黑夜的寂寥,我害怕听到更多悲伤的故事,我害怕时光会慢慢蚕食掉那些关于故乡关于村庄的美好记忆。
再见了,我曾经美丽可爱的村庄。多年以后,我还会回到这里,哪怕你已被历史的烟云所淹没!哪怕你已被众多的人们所遗忘!因为我的爱早已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许爱琼)
此文选自由嘉鱼县文化和旅游局、嘉鱼县作家协会联合编著的《南有嘉鱼》丛书。该书已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发行。